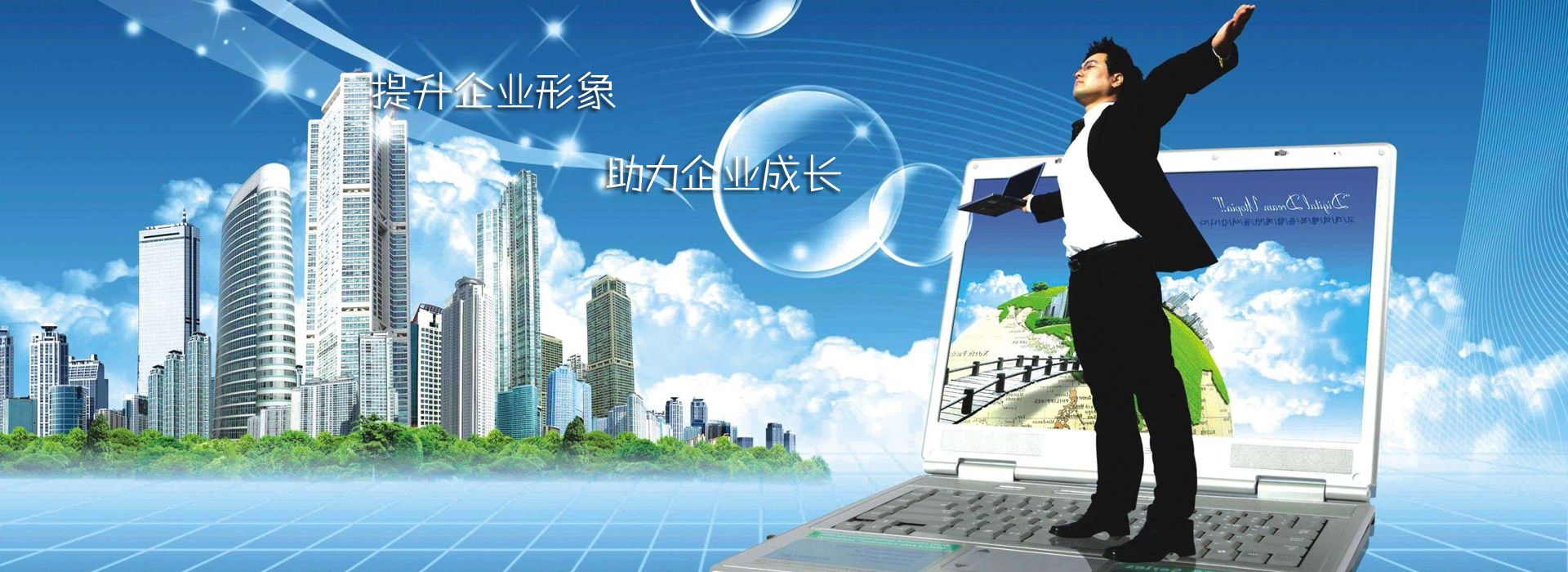互聯(lián)網不需要反壟斷
[大多數(shù)公司尚未認清這一基本事實,仍在盲目追求那些“放牧型”的商業(yè)模式。它們相信自己可以隨意地把網民趕來趕去,因而也就逃脫不了眼看著一個個模式覆滅的命運]
10月16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對360訴騰訊公司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一案做出終審判決:駁回360的訴訟請求,認定騰訊的行為并沒有排除、限制競爭,即不構成壟斷。歷時四年多的3Q法律大戰(zhàn),最終以騰訊公司勝訴而塵埃落定。
此案是我國反壟斷法頒布以來,最高法院審理的首例互聯(lián)網反壟斷案。被視為中國互聯(lián)網業(yè)壟斷者的騰訊,其遭際與世紀之交的微軟十分相似。
1998年美國司法部和20個州開始起訴微軟,稱微軟因在其以英特爾芯片為基礎的個人計算機上捆綁銷售視窗操作系統(tǒng)和IE瀏覽器,而濫用了壟斷的力量。這種捆綁被看作IE瀏覽器最終擊敗先驅者網景公司而在瀏覽器大戰(zhàn)中大獲全勝的終極原因。當每一個視窗用戶自動擁有一份IE瀏覽器拷貝的時候,與微軟競爭的瀏覽器的用戶卻不得不使用調制解調器費力下載,或是到商店去購買。
對此微軟的反駁是,視窗系統(tǒng)與IE瀏覽器的融合是創(chuàng)新與競爭的產物,兩種產品是一體的,消費者現(xiàn)在可以免費獲得IE帶來的所有好處。反對微軟的人則稱,瀏覽器仍是一種獨特和獨立的產品,不應同操作系統(tǒng)相捆綁。他們也表示,IE并非真正不花錢,因為其開發(fā)和營銷費用實際上打進了視窗的價格里,本來視窗不能定那么高的價的。
聽起來熟悉吧?騰訊將QQ即時通訊軟件與QQ軟件管理、QQ電腦管家等進行捆綁的行為是否構成反壟斷法所禁止的搭售行為?360發(fā)布的公開信正是這樣認定的:“中國互聯(lián)網產業(yè)巨頭壟斷捆綁的狀況,比起當年的美國微軟有過之而無不及。”
還有更熟悉的:和微軟一樣,與其說騰訊面臨的真正威脅是審理反壟斷案的法官,不如說動搖騰訊未來的因素在別處。
據(jù)360一方說,由于寡頭的存在,2005年之后的中國互聯(lián)網行業(yè),新的大型創(chuàng)業(yè)公司幾乎寸草不生。3Q大戰(zhàn),起始正是因為騰訊進入了360企圖獨霸的安全領域。然而,雖然騰訊仍在憑借即時通訊的強勢地位日進斗金,但它懷有微軟一樣的危機意識,不忘時刻警醒自己:當巨人倒下時,體溫還是熱的。現(xiàn)實中競爭者也的確在四處虎視眈眈:新浪微博把騰訊打了個措手不及,騰訊依靠微信才扳回一局;而隨著移動互聯(lián)網的全面到來,微信和淘寶將競爭未來最大的本地生活類O2O服務平臺。
不難理解騰訊對反壟斷訴訟的神經質反應——“起義者”一邊在市場上造反,一邊散播言論說騰訊的壟斷斷了它們的生路,政府務必加以干預。騰訊被迫在兩條戰(zhàn)線作戰(zhàn):一方面在法庭上戰(zhàn)勝對手;另一方面,確保騰訊在中國互聯(lián)網特定領域中的統(tǒng)治地位不墜。
在此,我們可以看出訴騰訊壟斷中蘊藏的一個深刻矛盾:如果騰訊支配了市場,它又怎么會在市場的強大壓力下不斷創(chuàng)新?如果壟斷者是一個扼殺競爭的“大猩猩”,新經濟又怎會變得如此富于競爭力,不僅提高了效率,而且促進了用戶體驗?在互聯(lián)網行業(yè),很多情況下,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企業(yè)的所作所為到底是壟斷還是創(chuàng)新,確實令人難以界定。
無論是微軟案,還是騰訊案,都使一個真正的問題浮出水面:反壟斷法是否適用于今天的技術競爭?這是所有關心新經濟的人都該認真考慮的。騰訊案是這樣一股力量:它迫使我們認識到,新經濟正在提出一些對社會有重大影響的問題,而政府和法律必須回答這些問題。
產業(yè)的死亡與新型競爭
新經濟不斷侵蝕舊經濟,但工業(yè)時代的思維卻徘徊不忍去。這種思維沒有看到的是,傳統(tǒng)的產業(yè)正在死亡。這并不是說我們要為水泥業(yè)或民航業(yè)的瓦解而默哀,而是說,產業(yè)作為描述商業(yè)活動的一個概念已不再有效,參賽者在界定明確的、永恒不變的產業(yè)里爭奪最高統(tǒng)治權的想法散發(fā)出腐臭味。我們熟悉的界樁到處都在松動,有些地方已成片倒塌。
替代產業(yè)的最佳說法也許是“商業(yè)生態(tài)系統(tǒng)”。一個商業(yè)生態(tài)系統(tǒng)橫跨好幾個產業(yè)。以微軟為例,它置身于四個大產業(yè)——個人計算機、消費電子業(yè)、信息服務業(yè)和通信業(yè)之間。
生態(tài)系統(tǒng)的概念來自于生物學。與生物生態(tài)系統(tǒng)類似,商業(yè)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特征是,具有大量的松散聯(lián)結的參與者,每個參與者都依靠其他的參與者,以取得各自的生存能力和效果。生態(tài)系統(tǒng)中的各參與者彼此命運攸關:如果生態(tài)系統(tǒng)健康,那么所有參與者都能繁衍生息;如果它不健康,所有參與者都會深受其害。
商業(yè)生態(tài)系統(tǒng)日益增強的重要性帶來了另一個重大變化:我們熟知的競爭也在死亡。最先觀察到這一現(xiàn)象的是詹姆斯.穆爾,他將生物生態(tài)系統(tǒng)觀應用于商業(yè)領域。穆爾在1996年出版《競爭的衰亡》,指出并不是沒有競爭了,相反,競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激烈,但我們需要重新認識競爭。傳統(tǒng)上,我們從產品和市場這兩點出發(fā)看待競爭,你的產品或服務優(yōu)于你的對手,你就勝利了,這將仍是重要的,但如此視角忽略了企業(yè)的生存環(huán)境:企業(yè)需要在這個環(huán)境中與其他企業(yè)共同發(fā)展,既有競爭,又有合作,這包括建立對未來的共識,組織同盟,談判交易,以及處理復雜的關系。
怎樣理解這個新的商業(yè)世界?讓我們回到生物學的隱喻上。在隔絕狀態(tài)下發(fā)展起來的真正的生態(tài)系統(tǒng),如夏威夷島上的動植物,極易受到環(huán)境災難的影響,甚至可能會大面積消亡。這與傳統(tǒng)產業(yè)極其相似:它在關稅、法規(guī)及利益集團的保護傘下活得似乎還不錯,一旦保護傘倒下就會面臨滅頂之災。與此相反,那些被一波波定居者侵襲的生態(tài)系統(tǒng)能發(fā)展出一種靈活的特性以抵抗災難。跨產業(yè)的商業(yè)生態(tài)系統(tǒng),常常表現(xiàn)出同樣的特性。
如果企業(yè)能夠看到整個畫面,懂得有時共同發(fā)展比互相爭斗更好,參賽各方也許都會變得更強壯。已故的人類學家格利高里.貝特森把生物共同進化描述為一個互相依賴的物種在無止境的循環(huán)中演進的過程:“物種A的變化為物種B的變化的自然選擇準備了舞臺。”反過來也是一樣。以鹿和狼為例,狼捕食體力較弱的鹿,使鹿群變得更強壯;鹿強壯后,狼唯有超越自己原有的能力才能繼續(xù)獲得食物。慢慢地,隨著共同進化的發(fā)展,整個系統(tǒng)都大為改觀。
新型競爭的最大特點是不確定性。傳統(tǒng)產業(yè)界限的消失意味著,企業(yè)會突然發(fā)現(xiàn),它在與不相干的對手競爭。最有創(chuàng)新性和進取心的公司在更廣闊的領域里施展拳腳,以新的商業(yè)生態(tài)系統(tǒng)改變了商界風景線。這些系統(tǒng)可能包括多種多樣的網絡和組織,其觸角伸及多個產業(yè),與其他類似的生態(tài)系統(tǒng)展開搏斗。
不停變換的陣線、迅速的技術發(fā)展和微妙的互依互存,使試圖靠現(xiàn)有的產業(yè)屏障抵擋外界對自己的生態(tài)系統(tǒng)的侵襲,成為徒勞無功的行為。你必須打破屏障,頑強地為生態(tài)系統(tǒng)爭取生存空間。這就是為什么微軟和騰訊這樣的巨無霸,要用自己手頭所有的力量打擊后起的競爭者。這也是在微軟和騰訊的狂轟濫炸之下,后來者仍有機會生存的原因。與其說微軟和騰訊和對手們在互相戰(zhàn)斗,不如說它們是在為自己不被淘汰而戰(zhàn)。勝利不取決于哪家公司擁有最好的技術,而是看哪隊人馬在高技術的轉動踏車上踏得更久。
在工業(yè)時代,勝利一度是以誰造出了更多的輪船、鋪了更多的鐵軌衡量的。在信息時代,勝利僅僅意味著能夠東山再起,明日再戰(zhàn)。無論如何,勝利與反壟斷無關。
用戶不是羊群
微軟的核心貢獻是為產業(yè)確立了標準。這意味著不必為多種操作系統(tǒng)開發(fā)應用程序,計算機網絡更易建立,人們在一家公司中學到的技能不會因工作流動而變得無用。對大多數(shù)技術來說,標準都具有決定意義。沒有標準,大眾化的市場將是不可能的事情。
標準有時是根據(jù)公司間的自愿協(xié)定而達成的,有時是在市場上決出的。一旦一家公司把持了標準,制止的方法往往是發(fā)明一種新的技術。在新技術面前,舊有的主導標準看上去并非堅不可摧。后起對手的目的也很簡單,就是要利用新技術建立新標準,將舊日老大擠出場外。
美國經濟學家布萊恩.阿瑟曾從打字機的鍵盤入手,研究標準的重要性。英文打字機和計算機鍵盤使用了一種鍵盤字母排列方式,這種鍵盤的左上角字母的順序是QWERTY。許多分析人員認為,按這一標準排列并不意味著效率最高。沒有一條法律說鍵盤必須這樣排列,但QWERTY方式卻行之有效。由于習慣的緣故,大多數(shù)用戶會執(zhí)著于這種標準,除非出現(xiàn)了某種特別好的排列法。
阿瑟將此稱為“學習效應”。由于高科技產品通常難以使用,培訓成為必不可少的一步。用戶使用QWERTY越久,熟練程度就越高,也就越難改用其他鍵盤。一家航空公司掌握了越多的有關駕駛、使用和維修波音飛機的知識,就會越傾向于訂購波音。這使得在市場上建立優(yōu)勢標準的產品能獲得更大優(yōu)勢。這個因素與消費需求而不是與生產成本有關。有些人可能會把這些市場稱為“自然的壟斷”,即在這些市場上,要靠一家生產商來提供最大的效益和方便。
所以,在互聯(lián)網市場上,從用戶的角度來說,他們需要壟斷。至少,在瀏覽器大戰(zhàn)中,IE是免費的。的確,微軟采取了一些強硬的手段迫使PC制造商采用IE。但誰能證明它的質量低于網景呢?騰訊也沒有依靠自己的壟斷而強行提價損害消費者的利益。QQ和微信都是免費的。凱文.凱利認為:“通常來說,用戶對于互聯(lián)網壟斷現(xiàn)象還是比較高興的,對此不高興的就是那些壟斷公司的競爭對手,而并不是用戶在抱怨。而且,我覺得這種網絡的壟斷是基于免費的基礎之上慢慢形成的,用戶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他們得到的服務總是在不斷改進,唯一抱怨的人就是競爭對手,而不是用戶。”
用戶有沒有抱怨的情形呢?有,在3Q大戰(zhàn)強迫二選一的時候。騰訊與360之間的不正當競爭,創(chuàng)造了許多荒唐的先例:比如,一個公開拿用戶來威脅競爭對手,展開一場荒謬的賭局:押注敢和QQ說“拜拜”的人比敢于拋棄360的人多,挾用戶以令天下;另一個則鼓動用戶揭竿起義,而大眾,則在此過程中成了博弈的棋子。又如,數(shù)億網民被迫投票選擇一個客戶端,用戶的電腦使用什么軟件由他人強行指定,在用戶的電腦桌面上展開“戰(zhàn)爭”,明目張膽地侵犯電腦用戶的權利。再如,作為中國頂尖的軟件公司,卻互相惡意修改、屏蔽、卸載,這也堪稱軟件發(fā)展史上的“第一”。兩家公司既不遵守游戲規(guī)則,又置用戶利益于不顧,這是整個中國互聯(lián)網的悲哀。
在“診斷騰訊”的時候我說過:“3Q大戰(zhàn)我對騰訊是持嚴厲批評態(tài)度的,當然我對360也是批評的態(tài)度,雙方都是在綁架用戶。互聯(lián)網時代,誰都不要以為自己可以永遠把用戶握在手里。因為很多公司往往都有一個心態(tài),可以稱之為‘放牧者心態(tài)’,它們特別希望圈一塊地,然后把用戶像羊群一樣圈在這塊地里。以騰訊為例,騰訊做的事情很多都不是著眼于改善自己的產品和服務,而是盯著競爭對手,如果這個競爭對手對自己圍起羊群的欄桿發(fā)起攻擊,自己就要想辦法修復和加固欄桿,不斷保持用戶在自己的放牧圈之內。這是錯誤的道路,正確的道路是想想你的用戶需要什么,你能給他提供什么,而不是時時刻刻盯著競爭對手。”
騰訊不能放開圍欄,而是以放牧者的心態(tài)固步自封,這是騰訊多年來曾屢遭詬病的癥結所在。在Web2.0時代生存的企業(yè),必須認識到一個基本現(xiàn)實:新的技術賦予個人前所未有的權力去影響互聯(lián)網。他們利用這一新媒體做什么,怎么做,和誰一起做,都是可以由他們自行決定的事情。利用網絡社區(qū)建設的應用工具,人們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愿望改造互聯(lián)網,而棄商業(yè)利益于不顧。
大多數(shù)公司尚未認清這一基本事實,仍在盲目追求那些“放牧型”的商業(yè)模式。它們相信自己可以隨意地把網民趕來趕去,因而也就逃脫不了眼看著一個個模式覆滅的命運。認識不清這一基本大勢的公司,哪怕你有著無與倫比的輝煌過去,只要你不顧及用戶獨立自主的內心,等待你的可能是一場巨大的失敗。彼時,再強的壟斷也救不了你。
所以,3Q大戰(zhàn)迫使騰訊走向開放之路,它或許是這場商業(yè)史上罕見的惡性競爭的最好遺產。在3Q大戰(zhàn)最慘烈的時候,我痛惜過:“用戶已死,有事燒紙。”但可喜的是,最終,“用戶為王”的道理還是被互聯(lián)網公司聽進去了。只不過,它們的俯耳傾聽并非緣于法律的強制,而是來自于用戶面對自身權益被侵犯時所發(fā)出的那種集體性的震耳的不滿之聲。